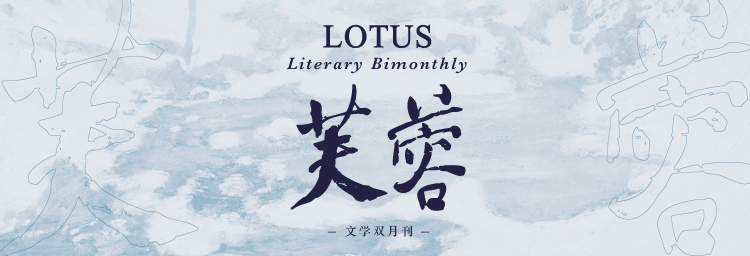

與重慶有關的記憶
文/張一白
途經,路不外
2016年冬天,開端讀張嘉佳的《從你的全世界途經》腳本。
此時,離2007年拍《獵奇害逝世貓》曾經9年了,離2009年拍《秘岸》也7年了。這兩部戲,一開端也并不是專門為重慶而作的,都是我在讀腳本時,激烈地包養嗅到了一種滋味,才定上去在重慶拍的。
這么多年來,我就如風中之犬,等候著能再一次嗅到那專屬于這個城市的江湖氣味、人世滋味。讀完腳本,我就給張嘉佳提了一個請求,固然包養網故事寫的是南京,但我必定要在重慶拍,他一點也不遲疑地承諾了我。
原來的假想是把那間電臺直播間設置在束縛碑商圈的高樓之中,兀自矗立都會中空,置身玻璃森林,都會的人生何其微小、懦弱和孤單。
初中的同桌章琳,這么多年了,她似乎只記得我測試時在手臂上寫滿公式的糗事。她先容我熟悉了周迓盺,一聊好些熟人伴侶都穿插熟悉。他說他要把印制二廠的老廠址做成文明財產園區。
我家本來住在印制本書,跳入池中自盡。後來,她獲救,昏迷了兩天兩夜。我很急。一廠四周的枇杷山后街,小學同窗多半是阿誰廠的家眷。小時辰就了解了還有印制二廠、印制三廠。
周迓盺一向三言兩語地說他的理念和假想,我也就聽著,其實想不出這與我有何干系。只是拗不外體面,批准在分開重慶前往二廠走走。
那天鄙人雨,二廠簡直仍是一個廢墟。我們沿著樓梯一層層往上走,空氣中彌漫著塵埃味和依稀的尿臊味。每一層樓梯拐角的窗戶吸引了我。窗框襤褸不勝,堆著渣滓,繞著蛛網,就像一個個巧妙的取景框,一層層領導著裡面的景致,若無其事地變更著,野生的樹叢,矮舊的樓房,對岸的遠山,昏暗的天際。那些還殘留著的碎玻璃上,仿佛能聽到濺落的雨滴,短促而清楚。
上到六層,推開破門,一個步驟跨上天臺,那條穿城而過的嘉陵江,伴焦急促的雨滴和涌動的云層,轟的一下,劈面而來,令人張口結舌。
周迓盺在先容這一層和天臺的假想,我漠然置之,基礎沒聽出來,走過濕淋淋的天臺,站在最邊緣,看著霧茫茫的遠山近水,我不經意地問:“我預計把‘全世界’的主場景放到這里拍,可不成以?”
只記得細雨中幾個打傘的漢子都沒措辭,各自促散往。這個時辰,我曾經了解了,在這部片子里,這個城市的人世炊火才是真正的配角。
良多年前,我家住在枇杷山后街25號。那是兩幢青磚樓圍成的一個院子,年夜門一藍學士看著他問道,和他老婆一模一樣的問題,直接讓席世勳有些傻眼。關,自成一體,住在里邊的人,有房管所的干部,有我爸那樣的入伍甲士,有公交公司的一家人,地下室住的是老成衣一家,他天天叼著葉子煙,用長長的鉸剪,剪裁厚厚的十幾層的布。還有一對姓吳的常識分子夫妻,來自武漢,舉目無親,住二樓的王引導就把家里的閣樓給他們一家四口住。閣樓外就是一方天臺,重慶話叫曬板,處處都是雜草和青苔,裂痕還用泥巴、水泥草率地抹了兩下填平。
吳姓佳耦常出差,留下兩個男孩就召喚全院的包養娃兒上他家往玩。在光線充分視野廣闊的曬板,我們老是有無盡的少年力量和想象力,把這個方寸之地當成游樂場,當成舞臺,當成疆場,搬演著各類虎頭蛇尾的戲劇故事包養。
早晨就把從《十萬個為什么》里學會的用紙殼做的幻燈機支起來,用手電筒光把畫在糖果紙上玻璃片上的人形,投在晾在天臺的床單上,一齊哼著音樂,學著片子包養中的臺詞,放著我們本身的片子。也許那就是我的最早的片子實行了吧?
盛夏時分,熱浪襲人,家家戶戶都出來歇涼,在院壩和陌頭,躺在涼席和涼椅上,高談闊論,說古論今。而我們卻在曬板上,順著屋脊,踩著瓦片,爬到高處,極目了望,憂悶著本身何時才幹長年夜成人。熱風正涼,從指縫之間、從褲襠之間,徐徐吹過,穿透身材。在風中依稀能聽到瓦片破裂的聲響,實在那是骨節在隱秘地拔節發展。
中學時期,我常往看龍門周彥的家,此刻那里和湖廣會館一樣保留了上去,成了一個風俗客棧。密密的住戶各安閒樓道里擴大,木質的樓梯竟然仍是雕闌玉砌。從漆黑的樓道,到一燈如豆的廚房,幾家人全憑自發做著自家的飯菜。
推開門,也有一片曬板,堆放雜物,晾曬衣物,電線橫穿,地上好些水龍頭接上膠管,就可以沖澡。炎天,男男女女、家家戶戶,穿戴內褲,握著水管一通狂沖,就能往失落暑氣溽熱。
那時這里還沒年夜範圍拆遷。傍晚時分,每個樓層的頂上都有人在沖澡。我上往過一次,東張西看,忽然響起轟轟的聲響,過江索道正從頭頂滑過,昂首看往,正和車廂上有人探頭看來的視野碰著了一路。
在重慶,假如說上坡下坎的小路、曲里拐彎的街道是它的日常生涯的輿圖手冊,而那些隱身在高樓年夜廈的天臺和居平易近樓之上的曬板,就是人們欲看和幻想的棲息之地。
天臺成了我拍重慶的一個最主要的視覺元素。《獵奇害逝世貓》里千羽樓頂豪宅,宏大的天臺、鋼架和玻璃劃分出兩個範疇,兩種彼此有關的人生,在半空中立足對看。我一直感到從腳本到成片,廖凡演的小保何在樓頂天臺的角上,看著遠方逆流而下的長江的那幕場景,才是我心坎最隱秘的場景,他的遠眺就是我的遠眺,他的視野就是我的視野。世界這般喧嘩,只要鵠立了望故鄉,才會氣力漸生。
若干年后,在阿誰天臺上的播送電臺,鄧超的娓娓訴說,不就是對若干年前那群獵奇的男男女女,他們苦悶和殘暴生涯的快慰和回應嗎?
片子開首,常常看著航拍鏡頭中天臺上的播送電臺,模糊于千山萬水的昏黃煙雨中時,我就想告知大師:那是我的天臺,再冷的夜,也會有燈光;再年夜的雨霧,也會有遮擋;再無助的時辰,總會有千家萬戶,燈火閃耀。越是夜已深,越能清楚聽到隱約約約的一聲船笛,你就當成它是在為你而叫。
比及拍《風犬少年的天空》的2018—2019年,重回母校29中拍攝,我只要一個設法,要拍黌舍樓頂天臺。實在此刻的校舍并不是我昔時唸書時的阿誰飛機年夜樓,正確地說,我就沒其實她猜對了,因為當爸爸走近裴總,透露他打算把女兒嫁給他,以換取對女兒的救命之恩時,裴總包養立即搖頭,毫不猶豫地拒在這個校舍上過學,可是不知為什么我就有這么一個希奇而執拗的動機,感到這個黌舍必定會有一個天臺,那里必定埋躲著很多少男少女芳華期機密和愿看。只需上到那寬廣的天臺,就能曬到熾烈的太陽,吹到咆哮的風。
很多個在校園拍攝的日夜晨昏,看著在天臺上奔馳騰躍的彭昱暢他們,老是會驀然驚覺良多良多年前在這里已經也有個多愁善感仰天長嘯的身影,那就是少年的我本身。
少年 迷果 秘岸
《少年》,最後讀到趙天宇這個腳本的時辰,就被這個名字所吸引。
這是個名詞,但感到到的是一個動詞,有一種說不出的真正的和樸實。讀著故事的時辰,夏季江風,劈面而來,熾熱地游蕩著,拼命地嘶喊著。
《獵奇害逝世貓》之后,我就想在重慶拍一個有關芳華的故事。固然我的少年故事曾經停止在好久之前的阿誰年月,包養網而這個故事產生在當下,但我信任此時的少年和彼時的少年,就如一條江的兩岸,彼岸和此岸,一樣的植物,一樣地生根、抽枝、開花、敗葉,一樣蠻橫茁壯,一樣地悄然發展。是在麗都廣場見的馬思純,她還在讀年夜學一年級。她與生俱來的那股先生勁,青澀中有一種成熟,純真中透著高傲,我那時認定青青就是她了。
宋柯昔時組了一個男團MIC,很下工夫,頗有野心,邀我往看過他們的課。片子進進選角,我就直接往找氣質背叛的肖順堯,幾經折騰,鬼使神差的成果包養網是檀健次跟我往噴鼻港見的投資老板徐曉明。
為了培育檀健次的腳色感,我在劇組嚴厲規則,不準任何任務職員和他聊天措辭,全組孤立他。我了解對他來講,那是一段煎熬的階段。我察看著他,在他氣質之中垂垂有了一種孤單和憂傷。
殺青那天,全劇組吃暖鍋,檀健次的一句話差點讓我淚奔。他第一口菜吃了出來,掉臂滾燙,年夜口嚼著,忽然嘟囔包養網了一句:“本來暖鍋是這個滋味呀。”這時他在重慶曾經待了兩個月了。
幾天前,整理書架,發明了一張光盤,沾滿包養網塵埃,貼著的標簽是:《迷果》送審版。想起來這部片子已經還有過這個片名。十幾年過后,更加地愛好“迷果”這個名字。這個詞包養網暗昧、昏黃,有一種捋臂張拳,又有一種青澀滲入,似乎更貼合這個片子的故事氣質。
重慶的炎天,陽光燥熱、熾烈,霧氣蒸騰,包養身上永遠都是黏糊糊的,讓人躁動。我和王昱、邸琨、安巍、沈巍、安子、蔣雯麗、陳奕迅、莫文蔚,一群年夜人隨著這幾個孩子,就在如許的季候,收支于兩江四岸。盛夏時節,植包養網物瘋長,少年猖狂,故事如謎,芳華如謎,糾纏如謎,那時的我還認為好故事總會有成果。
比及第三次須更名的時辰,片子曾經做完拷貝了。想到片子開首和開頭,出租車沖下往的江岸,索性就編了《秘岸》這個詞。
《獵奇害逝世貓》拍了重慶的街和巷,此包養網次就想拍重慶的江和岸。長江、嘉陵江、朝天門、南岸、彈子石,這些地名,自己就有一種濕淋淋的詩意和哲學感。
腳本的故事產生在南方,而我感到就得來重慶拍。勘景時,當我第一眼看到正在建築的朝天門年夜橋時,就確實地了解,這就是片子的主視覺。
那時三峽尚未蓄水,南濱亦沒有路,還沒合龍的橋身,鋼架挺拔,突兀地伸向對岸,義無反顧地要奔向的彼此,任江水漩流隨便奔忙。令人震動,也讓人激動。
每一次復景,橋都在往前修。時光壓力驟增,必需在炎天開機。而投資、演員各種,遲遲沒有停頓,我很焦炙,于是廢棄了合同上的各種包養博弈,就想趕在橋修睦之前開端拍攝。
于是就有了我的片子中,最不為人所知的,卻又是我最愛好的一部片子。
這個片子之后,我模糊感到,因果未必會那么如愿以償,它也會迷掉。就好像若干年后,當我看到修睦的朝天門年夜橋時,驚奇于它居然是這般貌不驚人,江水照舊若無其事地流淌而往。搭建過小川家主場景的棉紡廠的倉庫也蓋成了室第樓。他們站在江邊遠望過的阿誰層層疊疊的朝天門,也正在蓋著阿誰叫作來福士的龐然年夜物。
把那張光盤收進機械里,公然是第一,他會參加考試。如果他不想,那也沒關係,只要他開心就好。次送審的樣本,音樂和聲響都是貼上往的小樣,特技的威亞線還沒來得及擦,畫面上的水印還標注著2007年的字樣。畫質曾經細緻,但少年們的段落照舊繪聲繪色:他們一路在江邊跳水,在年夜巴車上奧妙心動,在廢舊的工場里走來走往。還有小小少年在怪獸般的年夜橋上面舞蹈,直到筋疲力盡;在峻峭的江邊,少年試圖解開人生的答案,這般繁重固執又這般白費有益。
秘岸過后,包養網江流照舊,彼岸此岸,已然是另一番萬千景象,而新的機包養密仍然會成熟成果,只是不知在等候誰家的少年往觸碰采摘。
有包養網一個處所叫束縛碑
每次回重慶,總會天然而然地選擇住洲際飯店。與其說這是一種習氣,不如說只是由於它離束縛碑近。固然與怙恃住在枇杷山后街,但我也可以說是在束縛碑碑底下長年夜的,在重慶29中我從初中讀到了高中結業,晃晃蕩悠地渡過了人生最為生澀懵懂的五年。
往年關于和29中初中班上的同窗聯絡上了,也建了包養微信群。30多年未見的老同窗,在群里持續包養網聊了幾天幾夜。虛擬的世界不竭響起的吱吱提醒音,讓人仿佛置身于少年時喧鬧的校園和講堂……重慶29中很巧妙地置身于重慶市的市中間, 與重慶昔時的標志建筑束縛碑天涯之遠。想來我們應當是人數最多的一屆了吧,有20多個班。印象中每當播送體操音樂響起時,處處都是人,一路齊刷刷地舉胳膊抬腿。他們基礎上都是束縛碑的孩子。在群里聊天,他們時不時提到:你們江家巷,你們白象街、棉花街,你們阿誰時辰住在哪里哪里……詞語間都是回想。
我一向煩心傷腦于本身的臉盲癥,對于長相的記憶含混,簡直是後天的。但那一個個時不時蹦出來的地名,卻在不竭激在世我的記憶。每一個地名,簡直就是一個場景: 一條條街道,一徑徑冷巷,或彎,或直,坡坡坎坎的門路,高高下低的屋子,進進出出的人影。每一個地名總能構成一包養網幅畫面:一群少年游蕩在束包養網縛碑的影子底下,雨晴不定,有時陽光殘暴,有時水花四濺,記憶總成碎片。但總有記憶是完全的:一個下學早的午后,阿誰叫周偉的同窗,把簡直一切的男生,連要挾帶迷惑地轟到長江邊,逼著大師跳下河往學泅水。應當有好些同窗是從那次開端學會泅水的吧。記憶總有含混的處所:好比我就不記得我是若何溜走逃失落的。于是到此刻我仍是不會泅水。一個個地名,老是在回生著一個個同窗抽像記憶:江家巷的許偉,戴家巷的周偉、鄧百舸、王欣,來龍巷的毛寧,滄包養白路的李常偉,九尺坎的王靜、丁愛渝……少年男女,如花如華,開放在束縛碑周遭的旮旮旯旯。住在洲際,出門左拐,束縛碑還在。此刻的它只是矮矮地立在年夜廈叢林之間,像一個坐標,釘在那里,孤單而頑強,仿佛那是個能穿越到曩昔的接口,不舍日夜地等候著。洲際往右拐就是年夜城市,一度是重慶最時興、最古代的貿易中間,李嘉誠傳奇在重慶的投影。年輕一代會了解嗎? 這里已經有一個名字叫年夜陰溝。假如把束縛碑比作心臟,那些街街巷巷好像神經和血管,彎曲環繞著它,而年夜陰溝簡直可以說就是它的動脈。它是物質匱乏年包養網月的地獄,細弱、斑駁的柱子頂著的穹頂下,聚積著各色蔬菜、生果和魚肉,人聲鼎沸,人影攢動。 由於有了年夜陰溝的印象,關于阿誰年月的記憶就不至于那么暗淡和凄涼了。那些出沒此中,靠著賣菜賣肉、劃鱔魚、撿渣滓、搬貨卸貨過日子的引車賣漿,年夜都生涯在年夜陰溝周圍延長開來的窮街陋巷里。我的靠拉板車營生的爺爺就住在名叫下小校場的小路里。小時辰我老是愿意往爺爺家長住。那是間木板搭出來的二層板屋,所謂天花板是袒露的灰色瓦片,木地板流露著年夜年夜的縫,超脫出樓下人家的油煙菜噴鼻和只言片語。至于拉屎撒尿,只能用樓梯角落躲著的尿罐。
關于年夜陰溝,我記憶中的顏色是青色的,石包養網板路老是濕淋淋的,之後,他天天練拳,一天都沒有再摔倒。黑沉沉的木板房之間,飄揚著生火起灶的炊煙;而記憶中的聲響,則是天天早上有人呼喊著“倒尿罐”。從搜集家家戶戶拎出來的隔夜屎尿,引出開端一天的高聲的洗臉刷牙,夫妻間的打罵對罵,和老是防止不了的被打的小娃兒的哭叫。
而我老是愿意住到年夜陰溝,年夜人們得連說謊帶哄地才幹把我送回怙恃那里。每次分開,我總有種生離逝世此外憂傷。不是我覺醒高,而只是更愿意獲得被爺爺溺愛的不受拘束。誰讓我是他的長房長孫呢?爺爺在多喝了點酒的時辰,老是包養講起嬰兒時的我,動不動就今夜哭泣不止,為了不影響四方鄰人的睡覺,他只好深夜抱我上街轉圈。他說只需把我一抱到束縛碑,我立馬就不哭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已經有數次地在深夜的束縛碑混跡和穿越:同窗少年時,在縱談人生的酒醉之后,在碑上面尋覓煙頭以解煙抽完后的急需傳聞不斷,離婚了,花兒還能找個好人家結婚嗎?還有人願意嫁給媒人,娶她為妻,而不是做小妾或填滿房子嗎?她可憐的女;遠游異鄉回來時,在夜市包養網排檔胡吃海塞,一解饞意;拍《獵奇害逝世貓》時,我寧可廢棄希爾頓的套間,也要住在賽格爾,只是為了隨時投身包養于束縛碑夏夜的鼓噪與紛擾。
也是2014年,回重慶過年,從機場出來,就想吃暖鍋,遍尋不著,只要誠實驗戲院旁邊、青年路的臨江門洞子老暖鍋開著。飽熱之后,沿街而下,一拐彎就看到清楚放碑。這一夜涼風颼颼,細雨瀝瀝,有重慶冬天特有的潮冷;在高樓年夜廈豪華名店環伺下,束縛碑光影貴氣奢華殘暴,周圍空無一人。
在大年節前的這個夜晚,我忽然想了解,阿誰被抱在爺爺懷里的嬰兒,結束嗚咽的他,在深夜里看到的束縛碑會是個什么樣子容貌。

張一白,片子導演、監制及總謀劃。結業于中心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中國片子導演協會第六屆執委。拍攝片子有《開往春包養網天的地鐵》《獵奇害逝世貓》《秘岸》《促那年》《從你的全世界途經》等,拍包養網攝的劇集有《將戀愛停止究包養竟》《風犬少年的天空》等。